完善驱逐出境制度 推进涉外法治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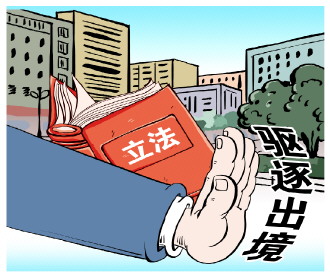
□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刑法中的驱逐出境因过去适用不多,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上升,入境我国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增长,相应的外国人犯罪也出现增长,驱逐出境的立法亟须完善。
现行刑法中驱逐出境刑事规定的立法不足
(一)期限不明
驱逐出境刑没有期限,造成与刑法内部和外部的其他相关规范不协调。从刑法内部看,别的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刑法对其期限有着明确的规定。从刑法外部看,我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行政处罚性质的驱逐出境规定了期限(10年),相比行政处罚,刑罚应当更严格、更规范,现有立法却没有明确的期限。
驱逐出境的期限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例如,缺乏具体期限使得驱逐出境无从并罚。依据我国刑法规定,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当附加刑种类相同时,合并执行。同时判处多个剥夺政治权利的,将剥夺政治权利期限相加执行。但数罪中即便宣告多个驱逐出境,也与宣告一个驱逐出境没有区别。再如,有的外国犯罪人在被驱逐出境后,旋即又进入我国,因刑事判决中的驱逐出境没有期限,导致犯罪者先前判决中的驱逐出境是否执行完毕成为疑问。
(二)适用范围不清
刑法只笼统规定驱逐出境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对驱逐出境具体应当或者可以适用于哪些犯罪未作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类案不类判,类似案件的外国犯罪人,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没被驱逐出境。
事实上,刑法学界大都认为,驱逐出境并非对一切犯罪的外国人都适用,而是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及犯罪人本人的情况等因素具体决定,其适用的实质考量要件是,外国犯罪人继续停留在我国境内是否会危害我国国家和人民利益。也就是说,刑法第三十五条的“可以”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理解为“应当”,即对于犯有危害国家安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等严重犯罪的外国人,或人身危险性高的外国犯罪人(如累犯),应当驱逐出境。但前述主张只是学理解释,既无法定的强制力,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立法的明确性问题。
(三)对附加适用的驱逐出境无法减刑
驱逐出境既可以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当独立适用时,驱逐出境不存在减刑的问题,因为对单处驱逐出境的外国犯罪人,一经执行便离开我国,难以对其是否符合减刑条件进行评估。
但当附加适用时,驱逐出境不能随主刑减刑而减刑,则会造成如下问题:首先,附加刑依赖于主刑而存在,只有主刑减轻而无附加刑减轻,会导致刑罚配置的不协调甚至附加刑重于主刑的局面。其次,减刑不及于附加的驱逐出境,不利于外国服刑人员的积极改造。减刑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当服刑人员的改造情况表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那么对原判刑罚进行适当减轻,这种减轻也应包括附加刑,否则其对犯罪人认真悔罪改造的激励就是不完整的。
驱逐出境刑事规定的立法完善
(一)确立驱逐出境的期限
在驱逐出境的期限上,可区分为“定期驱逐出境”与“终身驱逐出境”。
就定期驱逐出境而言,其上下限可以设为5年至25年。一方面,将刑法中驱逐出境期限起点设定为5年,主要考虑我国行政法中遣送出境的期限为1年至5年,这样可以衔接起来。虽然行政法中的驱逐出境期限为10年,但出境入境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均将行政驱逐出境的决定权赋予公安部行使,所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一般适用遣送出境,很少适用驱逐出境,而且建议将来把行政法上的驱逐出境统一纳入刑法中,以便彻底理顺驱逐出境的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定期驱逐出境的刑期上限设定为25年,既有满足刑罚裁量中的罪刑相适应的考虑,亦有缩小与终身驱逐出境之间距离的考虑,这类似刑法修正适当提高有期徒刑上限以便与无期徒刑缩短距离的做法,如为解决“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矛盾,根据修正后的刑法,有期徒刑最高可达25年。
就终身驱逐出境而言,由于其后果的严厉性,因而只宜附加适用于严重犯罪的外国人。具体可从两个方面来界定:一是主刑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外国人;二是实施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这三类犯罪且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外国人。
(二)明确驱逐出境的适用方式与范围
在驱逐出境的适用方式上,可分为“强制剥夺制”与“裁量剥夺制”两种类型,前者指依法应当适用驱逐出境,后者指根据犯罪人及其实施犯罪的情况可以适用驱逐出境。
“应当”适用驱逐出境的范围,可从犯罪类型、主刑的严厉程度以及犯罪人是否为累犯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在犯罪类型上,鉴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这三类犯罪直接侵害我国的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全,因而有必要将之作为“应当”适用驱逐出境的情形来规定(不论附加适用还是独立适用)。另一方面,根据主刑的严厉程度,对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外国人,也应当适用驱逐出境,因为就我国刑法分则的法定刑配置而言,配置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情节严重”甚至“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此外,基于特殊预防的需要,对构成累犯的外国人也“应当”适用驱逐出境。
“可以”适用驱逐出境的范围,包括可以附加适用和独立适用两种情形。对于“可以”附加适用驱逐出境的,宜界定为被判处实刑六个月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外国人,对这类外国犯罪人可由法官根据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等因素来决定是否附加驱逐出境;对于“可以”独立适用驱逐出境的,可将其范围界定为本来应当被判处管制、拘役或缓刑的外国人,因为管制和缓刑都是对犯罪人不实行关押,而拘役在执行中则允许犯罪人每月可以回家一至两天,如果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认为对外国犯罪人判处此类刑罚在我国执行有难度的,可以直接独立适用驱逐出境。
(三)构建附加驱逐出境与主刑同步减刑的制度
一是对附加驱逐出境的减刑与主刑减刑同步进行。附加适用的驱逐出境因依从于主刑,故其减刑开始时间和减刑间隔时间也都宜随主刑的减刑开始时间和间隔时间而定。当然,每次二者减刑的具体幅度无须一致。二是设定驱逐出境的减刑下限,设定下限主要是确保驱逐出境的特殊预防效果。具体而言,对附加判处定期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减刑后最终的驱逐出境刑期以不低于5年为宜,即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驱逐出境的法定最低刑期;对判处附加终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减刑后的期限以不低于15年为宜。
(四)将“不推回原则”等内容纳入驱逐出境
第一,对难民不得适用驱逐出境,包括已经正式取得难民资格的外国人和等待难民资格认定的外国人。第二,对可能在驱逐目的国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外国人,不得适用驱逐出境。第三,对与我国公民缔结婚姻或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外国人不得适用驱逐出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为贯彻“不推回原则”而设置的不得适用驱逐出境条款,并不是绝对的,当外国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时,可以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由,对禁止驱逐出境的义务进行克减,这也是有关国际公约所允许的。不过此时并不意味着要将该案中的外国人驱逐回可能遭受酷刑等危险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存在愿意接纳其入境的安全第三国,该国应成为驱逐目的国的首选。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