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爱国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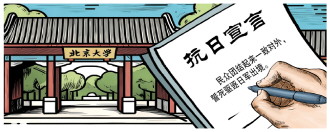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国民党北伐成功后,以新军阀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统治,推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不断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军队。可是,这时日寇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制造事变,几个月内,日寇的铁蹄踏遍东三省。蒋介石一方面畏于日本的军事强势,隐忍以待;另一方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遗余力地对共产党进行打击围剿。可是,日寇的野心越来越大,1933年春攻占热河,平津危迫。5月22日,日军更直接包围北平,离城仅数十里,坦克车四处横行,耀武扬威,气焰嚣张至极。军事当局恐有巷战,令各学校学生回避,于是各校“讲习都辍”。后因华北缔结屈辱的停战协定,各校得以是年秋季继续开学。
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刺激并深刻影响了北大法律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大学生会旋即组织“抗日委员会”,发表抗日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誓死驱逐日军出境。北大教职员组织“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商讨对日策略。分别于1931年9月21日、22日在第二院大学会议室召开“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法学院派周炳琳、戴修瓒两位先生作为代表参加,并由周炳琳先生担任大会主席。第一次执行会议议决推举周炳琳、胡适、燕树棠三位先生起草致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函电。函电内容主要有三项:(1)请严重抗议,要求日本立刻撤兵,恢复原状;(2)在未撤兵以前,不得谈判;(3)命令地方政府,不得与日本就地直接交涉。第二次执行会议推举各执行组主任,共分文书、事务、交际、宣传、研究五个组,其中周炳琳先生任交际组主任,燕树棠先生任宣传组主任,何基鸿先生任研究组主任,每组之间分工合作,共商抗日大计。9月24日,在三院大礼堂举行抗日运动宣传大会,教授胡适、何基鸿、燕树棠、陈启修、陶希圣、许德珩等到会演讲,对日军侵略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和谴责。
1931年12月,在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法学院教授陈启修先生发表题为《第二个“五四”》的演讲。他讲道:“‘五四’之后,中国的社会是天天变坏的……真真要想负担起拯救中国的任务的时候,必须以救国为前提,单单读书是不对的。如果想做了爱迪生才来救国,那时恐怕早已无国可救了。并且环境是否能容许我们读书呢?所以我们:(1)必须开辟我们读书的环境;(2)把自学未成焉能救国的观念改正;(3)必须自己起来从制度上改革。”北大同学要想真正继承“五四”精神,要想创造第二个“五四”运动,应当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争取“爱国自由权”;第二,争取“读书自由权”;第三,争取“大学自治权”。“只有获得了这三种权利,才能使救国者有真真的保障。”陈启修先生的演讲,对鼓舞士气、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巨大作用。
北大法学院其他教授学者们也纷纷发表文章,主张积极准备,抗战救国。陶希圣先生在《地方战与国民战》一文中强烈呼吁,“我们没有侥幸的事了,在今日,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战,才能够把国际的矛盾再扩大起来……我们要准备国民战”。张忠绂先生也公开发文,认为“可以战矣”。
日本占领东三省不久后,新闻媒体很快传出日寇拟在锦州设立“中立区域”的消息,一时舆论大哗。燕树棠先生特著文指出:“无条件的设中立区域等于断送东三省!”他在文章开头首先提请“全国注意”:“中国政府若是无条件的承认在锦州设中立区域,等于断送东三省,等于卖国行为,并且甚于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要求。”进而,燕先生提出主张:第一,反对无条件地设中立地带;第二,要求政府宣布设中立地带条件;第三,要求政府重修宣布整个的交涉方针!最后,燕先生向当时负责交涉的代表顾维钧发出警告:“我们现在警告顾维钧勿作章宗祥、曹汝霖第二!”燕树棠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发国人深省,有理有据,振聋发聩,不啻一篇战斗檄文。
对于像“九一八”这样的大事,北大法律系的期末考题中也有所反映。1934年北大法学院徐辅德先生主讲“国际关系及国际组织”课程,他出的三道考题中,便有两道直接关于“东北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徐先生出题时间虽距“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两年多,但由于相关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国人痛心,世界瞩目。在此之前,“国联”虽曾派代表李顿来中国调查事变真相,但是调查结果却含糊其词,无权也不敢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实质性惩罚,“国联”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徐先生出此考题之目的,笔者推测,不外乎要同学们关心国家和民族之命运,“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既要学到全面完整的国际法理论,更要为洗刷中国的耻辱而奋发图强。虽然不知当时同学们回答得怎样,但是这样的考题的确抓住了当时的国际热点,又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这既是一次常规的期末考试,也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国内形势发生转机,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日寇不断蚕食鲸吞中华大地,大战一触即发,“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日益严峻。当时北大有人记载道:“今之北平,已处边壤。一旦有事,首当其冲。此苟安之局不知能几何时……唯有益自淬励,期以学术上之成功为中华民族增光荣。书生报国之正,其在此乎,其在此乎?”
(文章节选自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的《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