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名例律》中体现人之常情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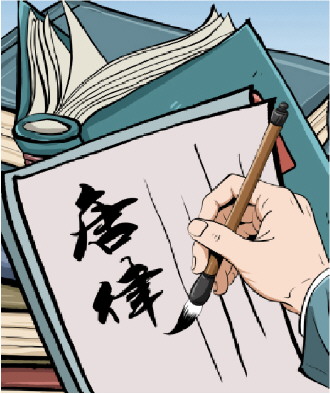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古代“名例律”的地位相当于今日刑法的总则,是《唐律》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的基本原则,注重兼顾“天理、国法和人情”,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关于“人情”,我在《“人情”的法理辨析》一文中提出,它有人的感情(喜怒哀乐等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人之常情(世间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人心(众人的情绪、愿望),人与人的情分(因血缘、姻缘、地缘等特殊关系产生的情缘),民间风俗,情面、交情,应酬、交际往来,馈赠八个方面的含义。《唐律·名例律》体现了人之常情的规定,人之常情即今日一些学者所讲的常识、常理、常情。
第一,古代没有社会养老和残疾人保障制度,所以养儿防老、家庭救助残疾人是当时唯一的办法。因此,在对罪犯实施刑罚时,不得不考虑谁来养老和救助残疾人的问题。
对为了当官而不去照料年迈多病的亲人,应该撤销其官职。《唐律·名例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应“免所居官”。意思是,祖父母、父母病老无人侍奉,抛弃尊亲而去担任官职,应该撤免其所任官职。
犯死罪和流罪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迈多病,家中没有21岁至59岁的成员,可以考虑特殊对待。《唐律·名例律》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诸犯流罪者,权留养亲。”意思是,凡是犯了非十恶的死罪,而且其祖父母、父母年老病重应有人侍奉,期亲内却无男丁的,可以上请皇帝减免刑罚。犯流罪者家中如有此情况的,可以暂且留在家中奉养尊亲。
第二,人才难得,自古已然。因此,古代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犯了罪,量刑时可以特殊对待。《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工、乐、杂户及太常音声人,犯流者,二千里决杖一百,一等加三十,留住,俱役三年……若习业已成,能专其事,及习天文,并给使、散使,各加杖二百;犯徒者,准无兼丁例加仗,还依本色。”意思是,凡是工匠、乐户、杂户及太常寺奏乐的人犯流刑,流两千里的杖一百,流刑每重一等加三十杖,不再远配,都服三年劳役。如果这些人学习已成,能从事相关工作,以及学习天文的,充当给使、散使的人,都杖二百;犯徒刑的,归还主管部门做本来行当。
第三,考虑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和未成年人心智自控能力较弱和今后再犯可能性不大两种因素,对其定罪量刑时可以特殊对待。《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一肢残疾等),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二肢残疾,双目失明等),犯(谋)反、(谋大)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意思是,凡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有疾病的人,犯流刑以下的罪,处赎刑。年龄在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患有严重残疾的人,犯谋反罪、大逆罪、杀人罪按法律要处死刑的,奏请皇帝裁决;犯盗窃罪以及伤害他人的,也处赎刑;对于其他的犯罪都不处刑。年龄在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处刑。
对犯罪时和发现犯罪时的年龄差异情况,《唐律·名例律》规定:“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意思是,凡犯罪时不属年老、残疾,而被告发时属年老、残疾的,以年老、残疾论处。如果在服徒刑期间成为老年、残疾的,也按年老、残疾处理。犯罪时年龄幼小,被告发时已经长大,按年龄幼小处罚。
第四,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血浓于水的感情因素,因此,古代允许家庭成员之间包庇一些特定的犯罪行为。《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意思是,凡是同居或比大功更近的亲属以及外祖父母、外孙或孙子的妻子、丈夫的兄弟、兄弟的妻子,有罪相互隐匿。即使给罪人泄露追收赃证的机密和暗中报告捕捉的消息也不受罚。如果小功以及比小功更远的亲属有罪相隐匿,比一般人的隐匿罪减三等处刑。如果上述亲属犯比谋反、谋叛更严重的罪,不适用于本条法律。
第五,对于法律规定有遗漏,但必须予以处罚,否则有失公平的行为,古代则允许比照其他条文来处理。《唐律·名例律》:“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意思是,凡断罪时没有明确的律条内容为依据的,如果要作出罪处理,就要举出比本案情节性质更重的事都作出罪处理的成例,来证明现在作出罪处理的正确;如果要作入罪处理的,就要举出比本案更轻的事都作入罪处理的成例,来证明现在作入罪处理的正确。这或许有不尽合理的“类推”色彩,但在当时却能够说服人。
由上可知,《唐律》注意把握按照人之常情定罪量刑,体现了法律要符合普通人良心和认知的规律。

 2025年07月23日
2025年07月23日

 2025年07月23日
2025年0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