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社会转型下中国环境法的挑战与因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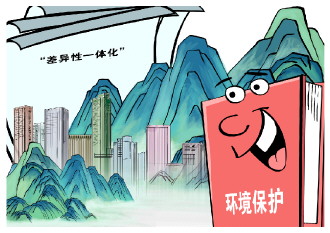
□ 秦天宝
双重社会转型下中国环境法面临挑战的深层逻辑
时空压缩是中国双重社会转型的底层逻辑,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被压缩至同一个时空之下,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问题在同一时空下发生大汇集、大碰撞、大融合,环境法的调整范围亦随之扩张。从时间方面而言,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解决损害防止问题与风险预防问题的双重困境,不同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历史的各种层次的褶皱。从空间方面而言,中国各地环境问题类型多样,城乡环境差异尤为凸显。由于二元户籍制度、污染产业转移、产业历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呈现出“城市环境趋向好转,乡村环境不断恶化”的二元化格局。
当前中国正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社会关系频繁流变,社会秩序日益复杂,社会风险无处不在,社会失范现象经常发生。具体到环境法,其表现为多元环境利益的冲突。在此背景下,中央与地方环保事权与财权的分配失衡,无法与环境问题的区域特殊性相适配,继而引发地方环境行政能力不充分与不协调的问题。而且,在科层式金字塔之下,保持高度向心力的环境立法、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朝着相同的方向齐步前进,这显然无法有效匹配区域环境问题的多变性,无法纾解不同地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的张力。
双重社会转型下中国环境法应对挑战的基本思路
“和而不同”理念的理论内核与实践理性是“差异性一体化”核心逻辑的集中体现。概言之,在尊重物质文明差异性的前提下,应追求各方价值立场、客观利益、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最大化统一,以实现万事万物在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自身运动与彼此互动的整体和谐。欧盟一体化区域共治模式与全球法律制度的统一化是比较法中的“多元一体”战略的重要表现。欧盟区域共治模式将“United in Diversity”奉为一体化的灵魂,核心是“多”中求“一”,“一”中有“多”。“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适用于国内法是‘变’与‘不变’的过程。”适用范围的扩张与语义内涵的变迁谓之“形变”。“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承载的普适价值与核心理念谓“实不变”。
“差异性一体化”的基本构成呈现出层层递进的逻辑主线,从“和而不同”到“多元一体”是从个体差异到整体认识的第一次蜕变,从“多元一体”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从共同责任到实质正义的第二次蜕变。“差异性一体化”内涵可大致区分为三个层面:首先,“和而不同”理念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相容,尚处于“差异性一体化”中“个体差异—相互尊重—个体差异”的第一层面;其次,“多元一体”战略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注重整体认同感,从而进入了“差异性一体化”中“此个体尊重彼差异—遵循一般(法律)原则—彼个体尊重此差异”的第二层面,但这尚处于应然层面;最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差异性一体化”较为成熟的阶段,追求一般(法律)原则与特殊个体相结合的实质正义,是对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的延伸,从而进入一般(法律)原则如何践行的实然层面。这也是“差异性一体化”中“个体之间尊重差异—在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提炼一般(法律)原则—实质正义的目标要求在实然层面对一般(法律)原则作出差异化安排”的第三层面。
运用“差异性一体化”思路实现央地(环境)关系的法治化,是其在中国环境法场域适用中的主要功能,亦是环境法转型期所直面的关键任务与时代课题。首先,要明确个体(地方)差异;其次,具有环境资源差异的个体(地方)相容于单一制国家(整体)之内,不同层级与不同地域的行政建制相容于同一科层体系之内,生态文明法治水平具有差异的地方相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内;最后,“差异性一体化”不仅在于个体之间尊重彼此差异,个体也需要在整体的指引下遵循一般(法律)原则,而且应当基于个体差异配置有区别的责任。
“差异性一体化”要求中央与地方在遵循共有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承载力、政府能力、司法环境等区域差异。中央与地方环境立法协同通过法律的层级关系和协调机制得以实现。“差异性一体化”要求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环境事权的明确化与合理化分配,与地方各级财政能力相适应。在中央与地方的环境政策层面,“差异性一体化”要求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允许地方在中央政策框架内,根据各地差异性进行顺应民众期望的、合法合理的、必要的调整。
双重社会转型下中国环境法应对挑战的具体路径
中央与地方立法协同的核心逻辑在于遵循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相对集权与适当分权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无论是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还是立法领域划分,都需以宪法为基础,确保环境法的整体性与体系性。而在环境法体系内部,则应调动地方立法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充分考虑地方差异,在纵向上实现权限的“突破”,以为中央立法的更新提供经验;在横向上实现领域的“跨越”,必要时可协调立法实现整体内的局部一体化,以服务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需要。
以时间为主线,在差异性层面,要充分认识新规范的独特性。新规范面向未来的属性要求行政的裁量权延伸至事前,亦会对法律保留原则、环境犯罪规范化归责原则等提出挑战。在一体化层面,要充分理解新旧规范的兼容性。要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将环境风险预防类案件与传统损害防止类案件的区别与联系具象化,而非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要在实践层面真正实现环境法体系的“差异性一体化”。
以空间为主线,应由“差异性一体化”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去引导全域、全类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规划的层级性、地域性、动态性要求地方尊重本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产业发展方向等,建立适宜本地的空间规划体系,通过规律各异的镶嵌组合形成国家范围内的空间规划。要在全域统筹战略指引下形成上下协同、尊重各地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差异的格局。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在生态环境脆弱性、自然资源储存量、经济发展条件等方面差异较大,优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应从系统性立法保障和差异性实质公平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基于生态补偿制度作为环境法经济激励中的重要内容,应尽早出台统一的、专门的、高层次的生态保护补偿立法,为我国形成生态保护补偿体系奠定法律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一套多领域的、全国范围的系统工程,需要立足现实,试点先行,注重实效,循序渐进。
跨区划间环境争端解决之道亦在于此,克服科层制体系下“条块分割”式的碎片化管理模式,结合实际情况与比例原则决定是否举行公开听证会,避免出现地方政府因封闭负外部性驱动而选择放松管制甚至转移污染等公地悲剧。第一,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检察力量直接立案,推广跨区划协作办案模式,在不同行政等级、不同行政区划内开展检检合作、检行合作。第二,风险社会下私人风险向公共风险的扩散要求环境司法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环境侵权救济,而应更凸显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第三,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在环境立法、环境制度的实施以及环境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4年第2期)

 2024年06月19日
2024年06月19日

 2024年06月19日
2024年0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