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原点的找寻
读散文集《写在庚子》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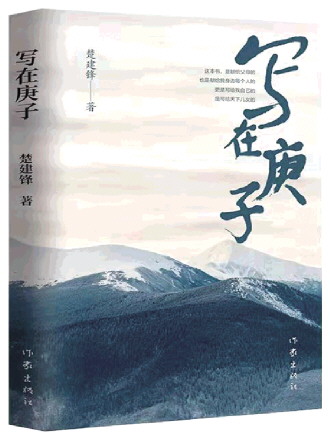
□ 徐安琪
案头放着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写在庚子》,作者楚建锋老师是几年前参加一个文化活动认识的。当时,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行政干部,待人真诚、作风严谨,但骨子里却有着文人的情怀。通过阅读《写在庚子》这本书进一步得知,楚老师还是一位高产作家,在庚子年、疫情期间的几个月时间里,边防疫边写作,写就了这部散文集。从作品中看出,他这种惊人的勤奋,源自他对亲人、朋友、工作和生活炽热的情怀,源自极端的自律。
作品中的相当篇幅,都在写自己年已耄耋的父母,情感是丰沛深沉的,笔触是生动细腻的。作者的父母这一代人,应该算是我的祖辈。几十年前陕南一隅的事情经他这样一描述,种种情形竟跃然纸上,时间的年轮清晰呈现,仿佛老照片活了起来,令人惊奇。
如是主题,让我想到《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番话:“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初次读到司马迁这篇名作时,我很难理解此番话的深意:人对父母的情感是自始而终的,为什么只有在困难时才会想到父母呢?近几年,经历了一些在社会上的起伏,才略有体会。人在顺境的时候,身边充斥着吹捧和赞扬,不仅俗务缠身,而且容易为浮华所迷惑;而当遇到逆境时,身边朋友所剩无几,一切繁华都被戳灭。此时,人仿佛回到了原点,便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只有源自父母的爱与支持,才是生而为人最本源的力量,才能支持人度过劫难。
就个人而言,包括楚建锋老师在内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遭遇职场上的大逆境。然而,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对整个国家社会乃至全球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灾难和困窘。人们被迫“关”在家里、慢下来,这种状态,又何尝不是对高速发展方式、浮躁生活方式的反思?在反思的节点上,让人追寻天道和人伦的原点,远离繁华、摒弃浮华、脱离矫饰,回归亲情、回归家务劳动、回归简单朴素的生活。
楚建锋老师在这个节点上陪伴自己的父母,撰写了回顾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往昔点滴,正应和了这样的哲学。
本书给我的较深印象,便是“情”和“悟”两个字。
“情”就是真情。书中记录了很多陈年往事和家庭琐事,但无不饱含作者的真情。带着满怀的感激去看待这些小事,便到处都是涌动的文学情怀。其实,每一对相伴一生的夫妻,都是一本传奇;每一个抚养子女成才的家庭,都有一部史诗。但能够留心且记录下这些故事的天下子女,实在是寥寥无几。难怪曹雪芹借《好了歌》感叹:“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楚老师就是一位难得的亲情回望者。
书中还有一些文章是应邀写人写事之作,或应朋友之邀,或应昔日领导之邀,甚至是应已故前辈的子女之邀。作者用自己的真情,用清晰的记忆和宏阔的视角,浇灌出一篇篇佳作。这些与当前工作并无交集、前途并无关联的师友,在他心中的地位却很重。在“利”字当头的社会,这些文字仍能传递出一种友谊的温度。
而所谓“悟”,就是作者的感悟。阅历的积累、职场的磨砺,让作者有了很多哲学感悟。譬如《爱情的距离》,就是一篇精辟的哲思之作,观点独到,能给青年人以启发。书中不少篇目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
书名为《写在庚子》,不禁让人联想到:60年前的庚子年1960年,新中国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再往前推60年,1900年更是国耻之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到了2020年,虽然举国遭遇疫情袭扰,但向上的国运已无可阻挡。从作者的文字来看,这些洋溢着奋斗的幸福的文字,正是国家走上复兴之路的写照。
国运好,家道方兴,个人才有了进步的空间,文运也能得到施展。无须赘言,请文友欣赏这本佳作吧!
(作者系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理事、撰稿人、北京大学校友)

 2022年01月11日
2022年01月11日

 2022年01月11日
2022年0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