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版权判定的认知经济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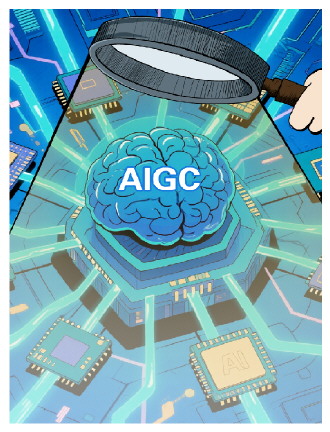
□ 蒋舸
用户能否取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以下简称AIGC)的版权?在探求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本体论层面的“名”“实”对应关系来探求何为“作品”,还应当在认识论层面考察不同作品观的认知经济性表现。
版权分析框架在文艺成果界权上的认知优势
从认知经济性的角度看,“作品”概念的功能是筛选出与版权法上利益平衡分析框架相匹配的信息成果。考虑到版权法在小概率文艺成果事后界权方面的优势,允许AIGC进入版权分析框架才是明智之选。不仅不应绝对化地把AIGC排除在版权分析框架之外,而且在设定可版权标准时,还应当将充分发挥版权分析框架的认知优势作为目标之一。
AIGC独创性高低判断的认知成本分析
版权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用户独创性贡献程度高到足以直接认定为作品的AIGC(以下简称高独创性AIGC),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用户贡献程度较低、但与既有作品和公有领域内容存在显著差别的AIGC(以下简称低独创性AIGC),因为区别对待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的做法势必产生高昂的区分成本,而该区分成本并不能通过区分收益得以弥补。具体而言,该区分成本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高独创性标准的选择成本
一旦拒绝适用“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决策者便面临在各种高独创性标准之间进行选择的难题。经验表明,与判断独创性的“有/无”相比,判断独创性“高/低”的难度更大,仅在各种高独创性标准之间进行选择本身就将耗费大量认知成本。
(二)逐个澄清创作过程的制度成本
如果将高独创性表达作为用户取得版权的前提,则必须在每起个案中调查用户贡献是否达标。无论是在前AI时代还是AI时代,试图针对每个文艺客体来逐一判断版权主张者的贡献程度的认知成本都很高。“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只关心人的贡献,不关心人的贡献与非人因素贡献之间的比例,因而能够回避逐一判断人类贡献是否主导的难题。这一认知成本层面的优势恐怕正是它能够成为全球主流标准的重要原因。AI的出现只不过使得人类贡献与非人因素贡献的混同变得更加明显,但并不会使得从混同物中区分出人的贡献并且判断其主导地位变得更加轻松。
对于版权登记机关而言,考察用户是否输入了作品、是否进行了汇编以及是否进行了线性修改都意味着对用户创作过程进行考察。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奉行版权自动产生原则,登记并非取得版权之条件,故登记机关不以实质审查为己任。如果我国在权利客体环节引入针对每起申请的实质审查,则版权登记机关需要逐一考察每个申请登记的AIGC的创作过程,这意味着对现有版权登记制度的重构。即便我国希望提高版权登记质量,逐一考察AIGC创作过程也不是对症下药的方式。
调查成本只是程序事项,与可版权性的实体规则无关,无论调查成本多么高、用户为了获得版权而隐瞒过程信息的可能性有多大,都应当将非源自用户的内容排除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外。这种将程序与实体截然分开的思路,恐怕难以反映许多规则背后的制度逻辑。法律规则设计乃通盘考虑之结果,实体规则的合理性不能脱离程序效率而存在。
此外,即便公权力机关甘愿容忍区分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的认知成本,公众面对的区分成本可能已然高到阻碍区分目的的程度。无论针对哪种AIGC,公众既不能从AIGC中看出用户是否输入作品,也无法看出用户是否对AIGC前序输出内容进行汇编或者线性修改。由于公众无法以合理的认知成本来区分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因此所谓公众能够自由利用低独创性AIGC的益处根本无法实现。由此,无论AIGC质量如何,公众的合理策略都是避免照抄。
(三)AI定制化导致的折中标准排除困难成本
区分成本高昂的第三项原因是,AI定制化将导致对低独创性AIGC的排除越来越困难。
AI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仅意味着机器越来越优秀,却不意味着人越来越无能。用户与AI的“双向奔赴”意味着,用户越来越可能以相对较少的输入获得比较满意的输出,这导致“线性修改说”和“实质控制说”的实践效果将越来越接近于“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
(四)持续记录与保存创作过程信息的社会成本
有学者建议法院在必要时可要求用户提供其AI客户端上存储的关于创作过程的记录作为佐证。但这种记录并保存创作过程信息的要求即便在技术上可行,也不应当被设定为用户主张版权救济的必要条件。
首先,绝大多数版权都不会成为交易或者诉讼的对象。由于用户未必能够准确判断哪些AIGC未来将被交易甚至引发纠纷,因此只能对所有AIGC的生成过程予以记录保存。由此产生的成本对于绝大多数并不进入交易或纠纷的AIGC而言毫无必要。
其次,版权保护期相当漫长。在如此长久的时间内维持AIGC与其创作过程信息的对应关系未必容易。
(五)新设规范的立法成本
国内外均有论文建议通过新增邻接权来实现AIGC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平衡。从认识论角度看,如果立法者为低独创性AIGC新增分析框架,则目的不应仅停留在维护“独创性”或者“表达”等概念的传统教义上,还应当追求提升认知效率的目标。这对规则制定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稍微不慎,便容易出现新增规范无用或者有害的结果。
AIGC独创性高低判断的认知收益分析
笔者之所以不赞同区分策略,是在综合考察社会收益之后,发现区分策略实为“华而不实”。
(一)拒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的策略缺乏社会收益
首先,独立创作不侵权规则足以确保公众的行动自由,所以拒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版权对于公众自由并无实质增益。AIGC都是小概率成果,所以即便承认用户就低独创性AIGC享有排他权,留给公众的创作空间仍然非常宽广。
其次,版权法上灵活的权利限制规则为公众自由提供了“按需定制”的实质保障,进一步降低了不保护低独创性AIGC的边际收益。
最后,恰当的权利救济力度应当与用户贡献程度相称,当侵权责任并不构成实质负担时,拒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也就不会给公众带来实质利益。
未来,运用AI将成为主流创作方式,相当大一部分内容生产行为都将以某种形式用到AI。在此背景下,否认AIGC可版权性无疑将把用户推向以下三种行为模式之一:一是放弃创作;二是放弃用高效的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创作;三是隐瞒对人工智能的使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的不合理性都足以督促我们谨慎对待“AIGC不受版权保护”的立场。
(二)为低独创性AIGC新设产权规范的做法缺乏社会收益
至今为止,未见有人设计出合理的低独创性AIGC分析框架。假如低独创性AIGC的分析框架实质上与版权分析框架一致,强求法官每当面对AIGC都要区分作品与邻接权客体的意义何在?区分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并给予不同待遇的制度成本不菲而制度收益存疑。因此,合理的制度设计应当对这种区分保持“理性无知”。
AIGC版权判定的规范建议
版权法的历史表明,原本形态各异的可版权性高门槛逐渐都已降低到“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附近。可见低门槛的法律预见性远胜高门槛。面对极低比例被卷入纠纷的AIGC,法院应当确保救济力度与用户贡献匹配。具体而言,需要贯彻以下规则:
第一,无论贡献程度高低,用户均不能禁止他人独立创作。第二,对于用户而言,提出关于创作过程的证据是权利而非义务。第三,当用户能够证明自己输入了作品、进行了汇编或者实施了线性修改时,便可享有落入独创性表达范围内的演绎权。第四,关于用户贡献的证据可以作为损害赔偿的参考因素。法院可以通过动态调整各领域、各层次作品的合理许可费区间,引导创作者与使用者展开合作,建构良好的市场秩序。
总之,在判断版权制度合理性时,认知成本和收益应当作为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AI用户版权所促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人的主体性应当在坦然承认工具效能的基础上发展。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5年第2期)

 2025年07月02日
2025年07月02日

 2025年07月02日
2025年07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