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意识形态法治保障体系的文化安全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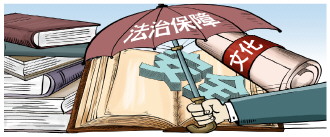
□ 张永坤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框架下,文化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正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关系国家精神命脉的稳定,也关涉社会意识形态生态的健康运行。
文化安全的深层结构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主权性,即国家对文化资源、话语权及其发展路径的有效掌控;二是认同性,指社会成员对主流价值观念的广泛认同与文化归属感;三是稳定性,即文化传播秩序不受外部破坏性干扰的能力。在数字化、信息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紧密,对应的法治保障需求也愈发迫切。
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协同
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密切交织,相辅相成。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是文化安全的核心指引。在文学、影视、游戏等文化产品中,价值观的表达本质上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渗透能力。若文化丧失意识形态引领,极易陷入价值混乱,进而影响国家认同与社会凝聚。
在数字技术深度介入文化传播的当下,两者的互动更加频繁且复杂。算法推荐既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也可能在无意识中放大边缘价值、亚文化乃至颠覆性信息。深度伪造、信息操控、话语污染等新型技术工具,使意识形态风险隐蔽化、扩散化。因此,必须从文化安全的高度统筹意识形态法治体系建设,打好主动仗、构筑防火墙。
文化治理赋能意识形态法治体系
推动意识形态法治保障体系建设,应充分挖掘我国深厚的文化治理传统。中华法系历史上始终强调“德法并举”“礼法合治”,体现出以文化为基底的法治思维逻辑。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治理不只是价值导向的输出方式,更是社会共识的生成机制。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普遍认同,其在制度建构和法治运行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因此,意识形态法治保障体系的构建必须注重文化治理逻辑的融入,形成“文化赋能法治—法治规范文化”的双向互动机制。
具体来看,应从以下三个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法治智慧:第一,德法共治的历史经验,强调制度与伦理、法律与道德的协同;第二,党纪严于国法的政治文化传统,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优先性;第三,家国同构的伦理基础,有助于在社会治理中实现“法理情”统一。
加强数字领域意识形态风险规制
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法律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法治框架。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文化传播环境,现有立法仍存在规范碎片化、条文原则化、覆盖范围传统化等不足,亟须加快专门立法与规则细化。
比如,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一条明确提出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但尚未针对文化数据(如网络文学、影视剧用户偏好数据等)的意识形态风险作出具体规定。《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虽对出版物内容设有审查机制,但以公众号、自媒体为载体的数字出版内容尚未明确纳入监管范围。
对此,应加快文化数字化领域立法进程,完善文化内容“负面清单”制度,细化意识形态风险识别指标,明确法律责任边界。推动实现从平台端内容审核到算法端推荐机制、从用户端使用行为到数据端风险防控的全链条法治覆盖。
构建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
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治理具有高度的跨部门、跨层级特点。当前,宣传、网信、公安、教育、文化等多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但也容易出现监管信息分散、资源无法共享等问题。
建议以“全周期管理”理念为导向,建立以宣传部门为核心,文化、网信、公安、教育等协同参与的矩阵式治理架构。开发意识形态风险数字监测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监管机制,实现从内容预警、平台干预到案件查处的全流程闭环处置。一旦出现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异常信息,各部门可快速反应,协同作战,防患于未然。
强化文化数据主权治理
意识形态风险不仅限于国内空间,更呈现出跨境传播、跨平台渗透的趋势。在全球文化交融与技术竞合加剧背景下,我国亟须增强对跨国文化数据平台的治理能力和价值引导力。
一方面,应针对境外平台向国内传播未受意识形态审查的内容、利用用户数据构建“价值画像”等行为,探索建立反制数据霸权的法律框架,从价值导向、伦理审查、数据主权、文化基因保护等方面制定相应规制标准。
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和数据治理规则的制定与合作,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稳定的外部制度环境。
文化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意识形态法治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支撑。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新特征、新挑战,唯有坚持系统思维与法治思维并重,从顶层设计、法律体系、技术治理、国际合作等多维发力,才能有效构筑文化安全的坚实防线,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迈向更高水平。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制图/李晓军

 2025年04月15日
2025年04月15日

 2025年04月15日
2025年04月15日